Abstract:
Glioblastoma(GBM) is a highly malignant tumor. Despite various treatment modalities, such as surgery,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most patients with GBM are still dying of its recurrenc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GBM is extremely poor, which is related to not only tumor cell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but also immature tumor monitoring methods. For a long time,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 can be detected in patients' blood. I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urrence of GBM. Therefore, the CTCs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glioblastoma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have been a hotspot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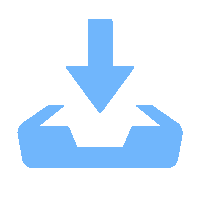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